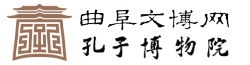生活儒学与当代哲学
提要:生活儒学与当代哲学的关系是:在当代西方哲学的三大思想运动中,生活儒学更接近于海德格尔现象学,但对后者进行了根本性批判,由此重新获得孔孟儒学的“生活”观念;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之间既有可对应性,又有非等同性;生活儒学承认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转换,但解构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还原到生活存在的本源视域。
今天非常高兴再次来到春城昆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云南师范大学。我第一次来昆明是上世纪的1981年,后来其实一直想故地重游。不仅如此,这里还有我的好朋友、老同学李广良教授,我们经常联系,他也经常来成都。我对他说:我很想再到云南去看一看,但是让我想起我们四川大文豪苏东坡所说的:“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我就属于“营营”的范畴吧,呵呵!总而言之,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今天终于来了,借此机会,我特别感谢“真善美书家”让我了却了这个多年的心愿。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生活儒学与当代哲学”。我先把“当代哲学”做一个简单的划分。记得我去年底(2008年)给《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稿子,谈的是“中、西、马的对话”,其中有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当代哲学的基本划分,及其基本形态、现状和走势,以及与中国哲学过去、未来的关系是什么。 今天晚上我想就着这个话题继续谈:那篇文章没有谈到“生活儒学”的具体问题,今天我进一步谈。那篇文章主要是讲从五四以后、特别是1923年“科玄论战”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分立为三足鼎立的三大派——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他们和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今天接着谈,就是谈他们和生活儒学是什么关系,这就更加具体一些了。
由此,今天晚上我会谈这么几个话题:第一,生活儒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这需要讲一些当代西方哲学的背景。第二,生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想说,可能我们所学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不完全是。第三,从中国哲学内部来讲,生活儒学和现代新儒学是什么关系。
为了谈清楚这三个关系,我先简单介绍生活儒学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生活儒学的基本内容
在座诸君当中,有的可能零星地读到过关于生活儒学的东西,有的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一个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致力于儒学的当下化,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找到一种思想视域,这种思想视域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当今世界、当今时代最前沿的观念;第二,它同时必须是我们的原典儒学、或者说原始儒学所固有的、而长期被遮蔽了的一种观念。如果我们能找到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平台,那么,在我们的心目中,孔孟以后的儒学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它们未必适应于我们当下的生存方式。于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这种新的思想视域的地基上,重建儒学——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这就是我这些年想做的工作,我给它一个总的标签,叫做“生活儒学”。
这些年来,生活儒学引起了学界各种各样的反应,好奇的最多,批评的其次,赞同的不多。我举几个例子。当年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孔子大辞典》,最近准备进行修订、增加词条,据我所知,他们把“生活儒学”列为了新增词条。我当然很高兴;但是他们把内容发给我看了一下,我也不太高兴:他们所理解的生活儒学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但这也是别人的一种理解,没什么关系。另外,像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和西方的一些社科研究机构有些合作研究项目,研究新世纪大陆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性学派,也把“生活儒学”列为其中一家。最近北大出版社要出一本书,是关于新世纪中国哲学的最新创获的,其中也包括了“生活儒学”,他们选了我的两篇文章收进该书,我当然也很高兴。总的来讲,不管是否同意,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生活儒学。
我们来看生活儒学的首要的问题——过去的说法叫做“破题”。从题面上看,有两个关键词:“生活”、“儒学”。
说到“儒学”,大家好像挺清楚的:孔孟之道嘛!其实未必那么简单。像我们儒学界,关于“什么是儒学”的问题也是讨论得非常激烈的,分歧很大。特别是“五四”以后,我们好像已经和儒学这个传统久违了,我们现在重新来继承它、发挥它,这需要对儒学有个底线的定位,但这现在还是很困难的问题。我后面会涉及到“何谓儒学”的问题。
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生活”。这更麻烦!我出去,经常有人拦住我问:黄先生,你这个“生活儒学”我看了,但是看不懂,你说的“生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只好简单地回答他:生活不是“什么”。这就涉及到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生活儒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当你问“生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先设的观念,就是生活是一个“什么”: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讲,它是一个“存在者”;用中国哲学的话语来讲,它是一个“物”;或者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它是一个“东西”。而我想说的生活,却不是存在者、不是物、不是东西,而是先行于存在者、物、东西的那种不是东西的事情。(众笑)所以我就告诉他: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在我的生活儒学语境中,它已经不合法。我这样说,他还是不明白,还接着问:那生活到底是什么嘛?我只好告诉他:这两千年来,我们习惯于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只能思“有”、不能思“无”了。就像老子讲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你得回到“无”。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待会儿再展开讲。
这就是说,“生活儒学”这个词语是很容易引起一些误解的。不光是上面那个问题,我再举个例子,最近有人跟我说:你这个“生活儒学”,台湾的龚鹏程教授早就谈过了。我和他说:龚鹏程教授是谈过,不过他所说的“生活儒学”意思是儒学的生活化、普及化,把儒学贯彻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去,而我所说的“生活儒学”和这些完全没关系。再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好朋友,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我去北京开会,他曾跟我开玩笑:“晚上没事一起吃饭吧?生活儒学嘛!”讲“生活”儒学,不吃饭怎么行呢!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理解。当然,他是开玩笑的,但是别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生活儒学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今天有必要先谈一下“生活儒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来回顾一下所谓的“传统儒学”。“传统”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比如说,“五四”创立了它的新传统,这也是一种传统。这里涉及到历史哲学的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马上想到马克思关于历史的五个阶段的分期,这也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模式。但是,我对历史哲学有个人的看法。比如谈中国历史,我会从不同的维度来谈。例如政治哲学的维度,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作为儒家理想的夏、商、周三代之治(不包括东周),是王权政治、或者说“王权时代”;从秦皇朝一统天下至于清代,是“皇权时代”;从近代以来至于现在,我们走向的是一个“民权时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它维度来划分。比如从家族制度来划分,王权时代是典型的宗族制,也就是宗法制;皇权时代是家族制,这不同于宗族时代的家、国、天下同构;民权时代既不是宗族制、也不是家族制,而是核心家庭的时代,但核心家庭不具有宗族或者家族在其时代生存方式中的基本社会主体地位,真正的社会主体不是家庭,而是单子性的个体——citizen。
你会发现,这三个时代之间都有一个社会转型,表现为“礼坏乐崩”、“名实淆乱”。简单说,就是原来三代之治的那么一种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坍塌了、过时了,于是另起炉灶,重建一套社会规范和制度。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它在观念形态上反映为中国观念史上的第一次大转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也就是从皇权时代转向民权时代,我们这一百年来也出现了新的“礼坏乐崩”、“名实淆乱”。因此,我们也和孔子时代一样面临着历史任务:重建社会秩序、社会规范,重新做出制度安排。这个过程,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一百年来也不断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谁也做不到一统天下。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对儒学做一种划分:(1)王权时代的王道政治的儒学;(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所谓“专制时代”的儒学,或者说皇权时代的儒学;(3)还有一种新儒学传统,就是“五四”以后、特别是1923年“科玄论战”以后的现代新儒学,这是现代性的儒学。这可以追溯到康有为,甚至洋务运动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些都是不同的儒学,这本身就体现了儒学的自我变革、穿越时空的禀赋。所以,我今天来讲“生活儒学”,需要对传统儒学作一个重新的认识和分析。
当今哲学界有一个比较前沿的观念,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 ,我把它叫做“原创时代”。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所导致的观念大转型,意味着轴心时代的到来,理性觉醒,人类开始建构形上学。在中国,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之后的皇权时代的儒学,按我们今天的哲学观点来看,是很成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从轴心时代以后,就习惯于一种思考方式,在座学哲学的可能比较熟悉,即:我们的所有的哲学,始终在处理“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发展到轴心时代,突然有一种觉醒,忽然开始问:我、你、他、万物——我们今天叫做“存在者”——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何以可能的?这在西方哲学中表现为所谓“拯救现象运动”:这些东西都是现象,它们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面对众多的相对的存在者——所谓“天下万物”,开始追究它们的终极根据,寻求这种“多”背后的“一”。全部哲学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找到这个“一”,再回过头来重新用“一”说明这些“多”是何以可能的。这在哲学上叫做“奠基关系”。于是你会发现,这两千年来,我们只会思考两类存在者及其关系,就是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的关系。纯哲学、本体论就是形而上学;它所支撑、所奠基的所有分类学科,如科学、伦理等等,都是形而下学,都是研究的存在者领域当中的某一领域。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每一物有其“所是”,而哲学所研究的则是“是之为是”。 这是“多”和“一”的关系。用《周易•大传》的话来说,就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天”是一个形而上者的设定,是终极本质;它显现为“多”——显现为“现象”。
20世纪的思想第一次突破了轴心时代的观念。我们发现,在形上、形下之间的关系架构之外、之前,还有一个更为本真、本源的思想视域被长期地遗忘、遮蔽了。因为不管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它们总是存在者;而20世纪最前沿的问题是这样问的:存在者何以可能?我们即使追溯到上帝,他仍然是一个存在者,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你只能有一种回答方式:存在。一个存在者之所以成其为存在者,首先是它存在。这就是说,是存在给出了存在者。于是我们思考存在本身。那么,存在本身是什么呢?不是“什么”。因为当你说它是“什么”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存在者、而不是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存在是无。于是我们说:这两千年来,我们——西方也是一样——遗忘了存在本身,或者说遮蔽了“无”;我们只会思“有”,而丧失了思“无”的能力——丧失了最本真的思想能力。在儒学内部,这个过程就发生在轴心期以后、秦汉以来的儒学之中。比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你会发现:它们始终是在“形上—形下”这样的思考方式当中。一直到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界,还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只会思“有”,不会思“无”,遗忘了真正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
我经常讲,“最近的就是最远的”,实际上,我们人类20世纪这种最前沿的思想观念,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在轴心期以及前轴心期就存在着的。比如从儒学来讲,在孔孟那里,就有本真的作为“无”、作为“存在本身”的思想视域,而后来被遮蔽、遗忘、曲解了。这么一种思想视域,我给它一个命名:生活。我在我的文章里做了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论证,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在孔孟那里,真正的儒学的根基不仅不是形而下的“礼”,而且也不是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在”本身——生活。
以上是简单介绍一下生活儒学的背景。我现在介绍一下生活儒学的大致内容。
其实,这两千年来的“形上—形下”的思考架构,它是可以存在的,是有它的道理、不可取缔的。比如说,形而下学有两个最大的领域区分:一个是关于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的,我们把它叫做广义的“伦理学”;另一个是为科学奠基的“知识论”。这就是形下学的两个最大的分支领域。这么来讲吧:人类如果还要过一种有知识的生活,就需要科学、需要技术,那么就得有知识论,尽管我们可以反对科学拜物教、科学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反对科学;另外一方面,人类如果还要过一种有规范、有道德的生活,反过来说,如果人类不想过一种丛林生活——像狮子、狒狒那样,那么就得有伦理学。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进化论传到中国,这个进化论不是达尔文主义,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基于对人性的一个设定,就是“趋利避害”,就是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类。它把人设定成这样的东西,我给它一个命名,叫做“动物哲学”;它在伦理学上的体现,叫做“禽兽伦理学”。自从这种进化论——就是“禽兽伦理学”——传到中国以来,我们有的中国人现在还不断地用它来教育人,它把人界定为动物,这样来理解人、说明人的行为。人怎么能是这样的呢!这是我顺便说说的当前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回到刚才的话题。只要你要过一种有规范、有知识的生活,那么你必得需要伦理学、知识论这两块形下学的领域。那么,进一步说,我们今天哲学上有一个应该是明确的、没有争议的结论:这样的一种形下学,不管是知识论、还是伦理学,都必须有一种形上学为之奠基;或者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说,必须得有一个对世界整体的承诺,也就是所谓“本体论承诺” 。当你对世界整体有一个承诺之后,你就有一个存在论或者本体论、形上学,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是不可逃避的。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比如,我现在建构一种叫做“生活儒学”的思想系统,我就面临这样的选择:
假定我走到一个极端,抛弃我们人类这些知识、规范,实行丛林原则,那么这意味着传统儒学都可以统统抛弃,就像“文革”对待儒学的态度一样——“破四旧”,而且为之奠基的儒学形上学、心性论这些东西也都可以抛弃掉。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态度。我刚才已经分析过,这样的一种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还得过一种有知识的、有规范的生活。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极端:现在是“礼坏乐崩”的时代,既然如此,我们就重新把原来的那一整套规范请回来,那样不就很好了吗?把前现代儒家所建构的一套制度规范拿过来用,不就完事了吗?这种极端,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这样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按照“原教旨主义”考虑问题的话,在座的所有女同学都应该回家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你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众笑)我们现在儒学界有一种“原教旨主义”倾向,这是很危险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儒家本质上是“革命的”,犹如“汤武革命”要“顺天应人” ,我们要顺应当下的、现代性的生存方式。
因此,生活儒学既不能采取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也不能采取原教旨主义的立场。那么,生活儒学现在既需要形上学、形下学,又不能把过去的照搬过来用,怎么办呢?很简单: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于是我们马上想到:要进行重建,就像修房子一样,你的地基在哪里呢?这也就是回到上面我们谈过的问题:形而上者、形而下者这些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这就回到了存在本身,找到了真正的大本大源。
真正的大本大源就是生活、生活的原初的本真的显现——仁爱。“问情为何物?”按照儒家的理解,这个问法本身就错了:情不是物,情先于物而在。作为“无”的“在”本身,既先行于任何形而下的存在者——老子所谓的“天下万物”,也先行于形而上的存在者——老子所谓的“有”。 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复归于无物” ——回到最原初、最本真的“无”的状态;然后呢,就是“无中生有”——这就是我经常说的20世纪以来哲学领域最前沿的课题。
所以,生活儒学的工作,首先就是要揭示这样一种被遗忘、被遮蔽的思想视域:作为“在”、作为“无”的生活本身,作为原初显现的“爱”本身,就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并且给出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由此而重建儒家形上学、形下学,才能有效地切入我们当下的生存方式,解决我们当下的生活问题。这就是我的全部的宗旨、思考方式和路数。
以上就是我对生活儒学的一些简单介绍。下面三点,我就来谈一下生活儒学与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者:黄玉顺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