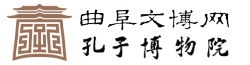济宁日报-孔林里的二月兰
编辑留言:
4月8日,本刊特邀我市作协主席孙宜才先生、散文家李木生先生与当地文友一起拜谒孔林,同以“孔林里的二月兰”为题作文。这是近年来继泗水、邹城、梁山之后的又一次同题写作采风活动,现将部分作品刊出以飨读者。此后,我们还将组织这类活动,欢迎更多文友参与。
●李木生
兰花,多有贵族。二月兰,却是世界上两万多种兰花里的平民。平民,当然易被忽视,常遭践踏,只是愈抑愈扬,再大的强力也按捺不住,蓬勃的生命就在七八千年里生生不息着。
如北大燕园中曾经伴着季羡林度过风雨的二月兰,南京理工大学冷杉园里常与市民耳鬓厮磨的二月兰,都是那样的气象独具,名传于世。可是,最能动我心魄又让我惊诧不已继而深爱不止的,还是中国曲阜孔林的二月兰。
清明前后,当你在夹道而列的千年桧柏里,走过一千多米长的林前神道,再穿过高大的红墙与森严的古侧柏相夹的长长的甬道,当你终于停在孔林门下,仰面注视着林门上古韵滞重的
“至圣林”三个篆体大字,正让胸间充溢着肃穆与沧桑之感的时候——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迈过这个短促而又高大的门洞,竟是一个如初生婴儿般清新娇嫩、又如新娘样羞怯热烈的紫蓝色的世界!二百多万平方米的二月兰,正怒放着扑怀而来,让你一下子投入在梦幻般的世界里,庄严的孔林更陡然亲切生动起来。
十万多座坟茔与四千多块宋元明清以来的碑石,尽皆淹没在二月兰的花潮里。随着墓坟层叠高低,这花潮便有了起伏的动势,仅只轻风抚过,就会掀起由近及远、又从远及近的紫蓝色的波涛。拥来漫去间,博大精深、绵延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孔林,便有了乘风破浪奔向未来的气象,每一座坟都成了一艘生命之舟,而那数十万棵或古或新、或翠或苍的树木,则成了扯起云帆的桅杆了。
人们也许会先入为主地直奔孔林的孔子墓园,而对这花的海洋视若无睹。但是二月兰自在地开放着,不求闻达,不谋地位,无欲则静地在天地之间释放着也享受着自己生命的美丽与快乐。
紫里泛着蔚蓝,蓝里透出着雪白,白里又浸染着淡红,全沐在春日嫩黄的阳光里,人就仿佛远离了尘世,神游于这彩色雾岚般的梦幻之中。这时,隐约着却是早已沁入在空气里与心脾间的爽冽和畅的清香,让人忍不住一次次深长地呼吸吐纳。这可是天上地下难以寻找的气息啊,草香,泥土香,树木香,去秋落入在草丛中的黄叶的香,全被二月兰的清雅之气酿成了一种非凡而又家常的圣洁之香。就连鸟的啼叫与太阳金色的光羽,都熏染着二月兰的味道。真的,玉石琴键一般的各种鸟的鸣啭,那片栖息着成群鹭鸶的柏树林的嗡嗡声,为枯木再生出俊美翠冠的藤叶的细细的沙沙声,还有风过耳旁时的呼呼声,都似乎漂粘着二月兰的淡却悠长的体香。于是,人就醉了,好像自己就是一棵浪漫而又自由的二月兰。莫非,吵嚷烦忧让人的本性异化了的现实只是一种幻觉?而我的醉与梦幻,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原色?
投身在这海洋之中以兰为伍并以心相交吧。每一株单一的茎上,都诞生着长幼有序的十七八个花的兄弟姊妹——最幼的米粒大小地绿着,有白苍的绒毛隐约在初绿间;稍大一点的花蕾,刚咧开星点的唇,闪烁着粉白的笑意;将开未开的,则将四片花瓣两两相叠卷成马蹄型的筒状,露着几分调皮与待放的急切。一旦开放,就如纵情展翅,那恣意伸展的四片花瓣,会让人以为是翩然的双蝶在飞,六枚微颤的金蕊则俨然是蝴蝶的须了。时有真蝶飞临,又恍若兰的开放,竟惹得蜜蜂绕追,缠绵不去。
久久地与之相伴,我与兰便有了关于飞翔的对话,絮絮地在风中——“有根扯着,还会有关于飞的梦吗?”“连焦黄的干叶子都会像飞鸟一样盘旋飞舞,何况我们花朵?开放就是一种飞翔,只要自由的灵性在。”“这样不加收敛地盛开,难道不担心盛极必衰后的萧条与落漠?”“萧条之时,正是我们果实成熟、弹出大量的种子并撒播于地下的新的孕育之时。”我仿佛看到了还没有来到的时间:不老的二月兰,正飞进明年的春天,飞进下一个世纪,也飞进美、自由与爱的梦里。
次第的开放,犹如前赴后继,也就能在一两个月里,不管晨昏,只见精神抖擞的二月兰,而不见它们的萎顿。看看它们,想想我们,光有采摘没有绽放的生命当是多么空虚与丑陋,而没有前赴后继争相开放的花蕾的生命,又是多么的寡淡与短促。以兰为镜,常常地照照自己,知美知丑、见洁见尘,真是不孬。
虽然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二月兰的绽放肯定还会经过艰辛与封锁的吧?在这片坟茔累累的死寂之地,是它们万众一心,奏响着生之交响。人世的黑暗是会将白日弄成黑夜的,它们的每一朵花,不就是一盏照世的明灯吗?这其中的悲悯与恻隐,点点滴滴,都洒在我的心上。孔林东部的林深处,我遇到了一个高不过腿肚的小坟,坟的周遭围着七八块砖,坟前只有三四片残石。看坟的颜色,当是最近十几年里筑下的吧。这里究竟埋着怎样的一个曾经被忽略与轻视的生命?只有二月兰郑重地生长在这个小小的坟上,在风中摇曳着,向着这个或许于孤苦贫穷中告别人世的灵魂,慷慨地开放着。这时,我注意到它们下部叶子的叶基处呈现出心形,而上部叶子的叶基则抱茎呈着耳状。莫非,二月兰们真的能够倾听、感知并记忆这个世界的欢欣与悲苦?
避开络绎的游客,一个人深入在花潮中,就会常常地遇见姿势各异的残碑,或扑或立着。风雨的剥蚀只会渐变出意味深长的沧桑,只有人为的残害才会造成如此让人惊心的毁坏。那是一个开花都要犯忌的“革命”年代,在这片林地里,罪恶比荒草滋生得还快。于是这里的每一座古墓,全被扒开,每一块古碑石,全遭到索缚锤击。印在这些石头上的二月兰的影子,当年就是与石头一起遭受着蹂躏。而今,还是二月兰在护着守着伴着,风里雨里、日里夜里,抚摸着无语的残石。
这些石头知道,二月兰们也是脆弱的,容易受到伤害。为了春日的绽放,其茎的底端几乎耗干了水分,而接近花序的上部,则又嫩又脆,饱满着血液般的汁水,一碰就断的。仔细看,青亮的叶面上,有的竟留有着斑驳的湿意,那是花的泪水吗?将心比心,我们应当献出着珍爱与珍惜,并让人与花的悲悯与恻隐交汇流通起来。
只是看似柔弱的二月兰,比石头更有着坚忍与柔韧的力量。那是个临近黄昏的时辰,我于孔林东部的南墙下,发现了一段奇异的景象,在不到三米宽的地段上,竟然同时排列着界线分明的四个世界:又高又厚的林墙,墙下是青叶绿蕾不见一支花朵的二月兰,紧挨着便是开得如火似锦的二月兰,再往北则是一行刚刚挣脱冬之寒旱、稍稍透着疲惫的柏树。二月兰没有柏树的四季常青,却能让一个一个活泼崭新的生命组成谁也无法扑灭的浩大的阵势。而林墙再高大威武,也无法挡住全部的阳光,跳出墙之阴影的二月兰当然尽着性子开放,就是处在墙的阴影之下从而晚开的二月兰,也是毫不退让,一直逼到墙的根部,不顾一切地生叶萌蕾。那种支支棱棱不怯不退的气度,那种迟早也要绽放的倔强,倒直白地捅开了墙之虚弱的老底。
今年大旱,又冷的时间久长,连松柏都现着些锈色。只有一株一株的二月兰,努力地生与长,在这死别之地生聚成蓬勃的紫蓝色的海洋,就连从林中穿过却早已干死了的洙水,也澎湃起紫蓝色的潮汛。洙水之阳,就是孔林核心的孔子墓了。这个生时尝尽了流亡之苦并让心里丛生着寂寞的布衣,最感欣慰的,也许不是每年九月热闹非凡的官办诞庆,而是每年清明时节二月兰用盛开对他的祭祀。在弱肉强食、狼烟不熄的时代,夫子曾经以身为烛,点燃起堪称先锋的仁爱的理想大旗。而今,孔林的二月兰开着,开成了依然堪称先锋的紫蓝色的旗帜。
孔林的冬之静雪、秋之红叶、夏之浓绿当然各有着非常的美妙,但是惟有这春天里的二月兰,已然成为一种“现象”,既能与乡亲百姓亲密无间,又可以感动润泽八方学人的心灵。改用唐人一句话,正可谓“生不用有名与钱,但愿一识二月兰”。
哪一天,我真的老了,痴了呆了迂了,只要有谁向我提起孔林的二月兰,我那浑浊昏花的眼里,也许又会爆起欣喜的火花。
●孙宜才
或乘车,或漫步,曾多次游览孔林,拜谒圣人墓,对孔子及孔氏家族的这座墓园,可以说相当熟悉。它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从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四月乙丑,葬鲁国城北泗上,子贡为老师庐墓植树,至今已有2500多年。最初孔子殁后葬此,墓地肯定是极小的,后来历代帝王不断赐田扩大,据说,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就对孔林重修、增修过13次,至清代已达3000多亩,成为我们目前看到的规模。林中的孔子墓、孔尚任墓、于氏坊等重要的文物景观,以及以桧柏、橡树为主的参天古木,错落林立的石仪石碑等,都使人印象深刻。可是,当文友打来电话,邀我去看孔林里的二月兰,我却一时茫然:孔林里还有二月兰?文友说,是啊,不但有,而且有两千多亩。我有些惊异了。不会吧,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于是我询问了周围几个对孔林并不陌生的朋友,竟都说不知道。岂不怪哉!
阳春三月,我随几位文友一起,专程造访、亲近了孔林里的二月兰。
穿过“至圣林”牌坊,一步入孔林,沟渠的堤岸上一片生动的紫色便跃入眼帘——这就是了,我们即将会面的二月兰。再放眼向远处眺望,嗬,整个林子里,全都开满了二月兰,嫣然一片花的海洋,犹如突然升腾的团团紫色的雾岚,簇簇拥拥,熙熙攘攘,在和煦的春风里轻轻摇荡。
当同行的朋友们纷纷扑进二月兰的花丛,急切地亲近那紫色花朵的时候,我还在兀自疑惑中:孔林里果然有大片的二月兰,以前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是来时的季节不对,还是被朝圣的虔敬所冲淡?这样想着,我漫步至一片正值盛开的花丛里。就在俯身细赏之后,我似乎有了答案:二月兰,实在太平凡、太不起眼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着突出的墓葬主题的园林里,被人忽略,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是啊,你看那细瘦的茎干,略显狭长、说不上什么形状的绿色叶片,还有那薄如蝶翼、仅有四片的十字形花瓣,以淡紫色为多,有的略显粉白,有的偏重紫红,似乎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连那花瓣上的筋脉也是干瘪的,似乎缺少肥力的营养和雨水的滋润,显现出它的贫瘠和细弱。不错,在争奇斗艳、千娇百媚的花卉的大家族里,二月兰既谈不上高贵,也算不得艳丽,甚至带着些贫寒,显得卑微而低贱。据介绍,这是一种非常泼实的野生草花,对自然环境和生长条件的要求极低,平原,山地,路旁,沟边,树下,有点空隙,就能密密麻麻地蹿出地面,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而且耐寒冷、耐干旱,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可是,在姹紫嫣红的花的世界里,除了雍容华贵的牡丹,浓艳欲滴的玫瑰,香气袭人的丹桂,娇羞如缕的芙蓉,还有那落落大方的粉荷,以及多得数不过来的奇花异卉——除了这些之外,二月兰,不是也自有它独特的风姿与神韵吗?二月兰,在还没见到它时,这名字就使我感到格外亲切了。一听,便能感受到它浓郁的民间气息,纯朴而素淡;便能想见那山野的姿与色,天然而率真。它不争艳色,不抢风头,淡泊明净,宁静幽远。它不卑不亢,自自然然,不刻意取悦于人,更不会露出谄媚之色。它没有丝毫孤芳自赏的扭捏作态,就那样任意挥洒着大自然原生的率性与纯真。它虽处荒僻,少有人注意,却没有自卑,也没有“寂寞开无主”的悲廖,更没有“黄昏独自愁”的哀叹,相反它以顽强、独立、自信的姿态,随处而生,遍地开放,有土地在,就有它的身影在,它默默无闻地开着,怡然自得地香着,开得热烈,开得奔放,开得疯狂,直至开得铺天盖地,弥漫天涯,淋漓尽致地开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春意,渲染出满世界平凡而质朴的美丽,将一腔紫色的魂魄回荡于天地之间!
朋友们纷纷举起相机,拉近镜头,拍下二月兰蝴蝶翩飞般的俏皮风姿;推向远景,留下那一片片摇曳起伏、紫白相间的雾霭;然后,把自己融入到那浓重的雾霭里,与二月兰亲密无间,挽留住一缕缕淡紫色的幽梦……
孔林,原本是别一个世界。这里墓冢累累,碑碣林立,石仪群列,亭坊飞翼;古柏老橡、虬藤朽枝之间,盘桓鸣唳着苍鹭泣鸦。我的一位同窗曾写过一篇散文,描画了孔林的苍凉美。不错,孔林是苍凉、肃穆的,甚至于有些阴森肃杀,这是孔林的主色调,也是“至圣林”不可动摇的主题。可是眼前,在这个明媚的春季里,这一切,都被二月兰流泻的海洋般的潮水淹没了,苍松翠柏下,累累坟茔上,墓碑旁,亭坊边,沟洼处,坡地里,全都铺满了盛开的二月兰,墓、碑、藤、木都不见了,满眼都是二月兰粲然的微笑、翩然的起舞,这笑容和舞蹈,全然将这里变了个世界,换了个主题,以至于墓地苍凉肃穆的气氛荡然无存,天地间洋溢着锦绣般的热烈与绚烂,透明的空气里飘荡着丝丝淡淡的芬芳,曾经是阴郁的大地呈现着鲜活有力的脉动和勃勃生机。
继续前行,走进孔林的深处,更有大片大片的二月兰陆续涌到眼前。煌煌以千亩计的二月兰,这在别处是罕见的,我早已被这一望无际的花海的壮观所震撼——谁能想到,每一株都是那样瘦弱、卑微、低贱的二月兰,一旦汇聚成几千亩的阵势,一起怒放,竟能成就如此壮观的景致,爆发出一泻千里的气势,宣泄着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力量!
如水的二月兰。此刻,我想到了载舟覆舟的水。真的想不到,二月兰,竟然与水有着相似的品格。
●裴存刚
这一次去孔林,是专程看二月兰的!
虽然从小生长在孔孟之乡,沐浴着圣人脚下的阳光,但这却是我第二次来孔林。第一次,来曲阜访友,因朋友家住在孔林附近,酒过三巡,喜欢文学的这位朋友力邀我前来拜谒孔圣人墓,那一日,血色黄昏,我们默默地站立在圣人墓前,静静地呼吸着千年古柏的清香,聆听着穿林而过的鸟鸣,虔诚地在孔夫子的墓前鞠上一躬,匆匆来然后匆匆去。心有余味然后又心有不甘,总感觉对孔林的感受相当肤浅,像唐突了圣人一般。
然而这一次孔林的二月兰却真切地触动了我的灵魂。
踏着阳春时节的暖风,沐浴着和煦的春之骄阳,跟随几位我特别尊敬的文学师友,再次来到了孔圣人栖息的永恒之地,刚进门,一种素未谋面的大美立即迎面扑来。林荫之下,满地盛开着淡紫色的小花,一团团、一簇簇,或立,或仰,或卧,微风拂过,一队队紫色的小花像统一着装的小学生,在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仿佛又看到了万名学生集体诵读《论语》的壮观景象。
这就是二月兰吗,一片片从脚下铺陈开去,向四周蔓延,无边无际。这样美,美到蚀骨、美到惊心。
三千亩孔林地,三千亩兰花开。
在这里,除了墓碑,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坟头。因为,所有坟茔和那些逝去的生命,都睡在二月兰的绿荫和笑靥之下。这似乎不是一个古老的墓地,而是一个花的海洋,花的世界。二月兰,开得这么好,这么多,应该算是一种奇迹吧!
常听人说,孔家是“文章道德圣人家”。按照惯例,文人骚客的墓前,人们会时常送来玫瑰花与康乃馨。孔林里没有玫瑰,但有遍地盛开的二月兰。这些开得鲜活而娇艳的二月兰,大概是上苍专门安排的对孔家逝者的祭奠和怀念。
孔林里有万千的故事和永恒的哲理。他把一个个传说带入地下又留在了人间。无论是千载之后依然在石碑上悲伤落泪的子贡,还是百年已过仍然苦苦挣扎在皇帝和山水之间的孔尚任。时过境迁,陪着他们默默等待的除了那静静的洙水河,默然不语的石像,就是这一片片的二月兰了。二月兰是寂寞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他的芳香、他的美丽,也许真的就只献给这些寂然不语的逝者。
可是,二月兰却喜欢这样一种寂寞,他像一个清高的文人,挥洒着自己的美丽,哪怕面对的全是这些无法言语的逝者。
每年,二月兰总是悄悄地开,又无声地落,他从不攀龙附凤,并不因为权贵到来而如此热烈,也从不因为平民的欣赏而平淡。他一如孔夫子留下的文人气节,求真、求纯、不媚人、不媚俗。
千年已过,逝者成灰。洙水河偶会干涸,千载的石像也有凋落,然而唯有这二月兰,一年一年静静地在圣人的墓地上守护。也许那众多的逝者耐不住地下的寂寞,希望借他看一眼那留恋过的蓝天,嗅一嗅那人间烟火。
走了大半个孔林,在孔尚任墓前驻足。这位孔夫子的后裔,当年因撰写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故事,得罪了朝廷,从朝中高官,被贬为贫民,流落孔林附近的石门山。
当时,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时,曾有好友提醒他,书中内容,可能会触动皇帝的神经,建议他改一改。但是,孔尚任明知朋友说得有道理,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坚持。
据说,孔尚任写《桃花扇》时写得很投入也很辛苦,以至有时屋外鹅毛大雪,室内的他依然摇扇苦吟。这种精神,或许正是兰花形象的另一种写照吧。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软骨文人,但是也总少不了像孔尚任一样的文人壮士。他们像遍布三千亩孔林的二月兰,脚踏充满死亡气息的土地,昂然而立,向天地展示自己人格的魅力。这也应该被称为一种大美吧。
记得有人写过这样一段话,乳房,是人死后最容易腐烂的地方;可是,在离她最近的心脏,却生长着不朽的思想。在孔林,这个埋着无数先人尸骨的地方,生长着灿烂的兰花,生长着文人赖以成长的湿润土壤。
寂静与庄严。三千亩坟地里,二月兰在轻吟低唱。心静如水的土地上,散发着泥土的色泽与花香。
●高永
倘若你的心还没有安顿之地,就去孔林看望二月兰吧。
我去看她,是个初春的早晨。转入千米神道,看到相传中的七十二贤古柏仍满面肃穆地在那儿侍立,亘古不移的传达着深刻,空气像是陡然间比城里稀薄了些,迅速凝结了身后的喧哗。
清明前后的孔林,绝对是二月兰的天下,仿佛一天的繁星,全部跌落在这座天下第一号氏族墓葬丛林里,化成了铺天盖地的二月兰的壮观景象。微风吹过,远远近近便涌起蓬蓬勃勃的紫色的烟霭,淹没在梦境一样烟霭中的碑石、坟茔也便有了温柔活泛的气息。
二月兰两年一生死,一年一盈亏,据说我赶的是小年,花势花期都不如去年。尽管如此,偌大个孔林,有土的地方就有她的身影,任凭柏、桧、柞、榆、槐、楷、等各类大树,盘根错节,她们自是不退不让,将花潮开了个辽阔无际。当然有着寒冷的逼迫,有着干旱的压榨,她们不管不顾、不畏不惧,只将小小的种子生发成燎原之势。广大着却又亲切着,低矮着竟又深厚着,隐隐地就有一种看不见的气场感染着你渗透着你。无意间,就会不由地向她泊靠,想蜷伏在她的脚边偎依着她,甚至干脆就有了投入在她的怀中的冲动。
这时候,一脸笑意的二月兰,就有了母亲的模样,向着这个干涸的近乎寡味的世间,亮出着湿润的、有着青草香味的母亲的心肠。
残石,枯树,还有挤挤挨挨在这片林地中的苦过的灵魂,便都有了依归一般,生长出了嫩绿嫩绿的芽苞。连那条延续孔家血脉的洙水河,也朦胧起淡淡的又浓浓的紫色的梦。
谁说时间的齿轮像长逝不已的水流一样无法倒转?四瓣的二月兰,正一朵一朵组成着一种另样的时间的齿轮,带我逆流而上,徜徉于往日的光阴里。那个作为妻子与母亲的颜徵在正在向我迎面走来。当她还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是命运牵她到了长自己四十多岁的叔梁纥手里?虽然司马迁的一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把她界定在了不合礼仪的另册上,但是也给后人多少带了些想象的浪漫。我是相信她是有着爱的,不然我猜不出三年的婚姻生活如何让她撑得起一生的孤独和寂寞。更令我唏嘘不已的,还有她对于儿子孔丘的大海般的母爱。没有这种不顾一切而又真正坚韧的爱,她又怎能在平常日子里节衣缩食、养蚕织布、忍辱负重地独自将息,让那一豆灯光撕裂长夜消磨掉葱绿的年华?只有爱才能让灵魂不坠。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子?浩瀚的史册里无解,也许人的有情只有放在无情的沧桑之中,才看出光鲜,情这个字不知灼伤过又滋养过多少女人的心灵。人生苦短,正是三十五岁便香消玉殒的颜徵在将一个爱字演绎得格外惊心。
放眼孔林,如果说孔子及其两千多年间的男子们如这林中的松柏立起着历史的骨架,那么,我要说,颜徵在及其两千多年间的女子们,恰似这生动的二月兰,丰满着历史的血肉。
时光,重叠在一枚枚花瓣上。正午的阳光花般地开着,阳光中的二月兰便有了一种且柔且刚的妩媚。
走出孔林,一步三回首,那霭霭着母亲容颜的二月兰便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永也不会停息的紫色的波澜……
稿件来源:李晖摄